
1932年,马林·罗帕斯(Marian Ropes)在美国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综合性医院内,建立了第一所特别注重于狼疮的关节炎病房。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诊断狼疮的血液学专项检测。事实上,直到1948年,除了外用药膏和阿司匹林外,狼疮病仍无有效的治疗用药。据当时罗帕斯(Ropes)女博士的观察,大约半数病人在治疗的2年内病情好转,而另外半数病人则因病情加重而死亡。如是,该博士便将狼疮患者分成为“脏器损害型”和“非脏器损害型”两大类,但许多病例并未做病变组织的病理学检查,因此不能确定患者的此种分类是否可靠,也不能准确肯定每例患者到底应归于哪一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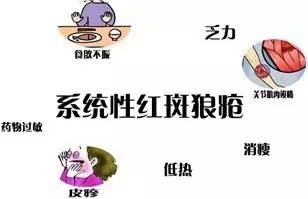
1946年玛约(Mayo)医院临床病理学家马可姆·哈格拉维斯(Malcolm Hargraves)对一例病人进行骨髓检查时,心不在焉地将一个装有骨髓标本的试管放在口袋内达数日之久(骨髓检查通常从胸骨柄或骨盆前、后上嵴或腰椎棘突抽取骨髓标本),在哈格拉维斯从口袋内取出装有骨髓标本的试管后,病理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标本涂片时,看见了一种独特的细胞:一种吞噬大量紫红色包涵物即抗核抗体的嗜中性白细胞。该学者在1948年发表的红斑狼疮细胞的论文可称得上是风湿病学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这种细胞是在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时全身多脏器发生了活动性炎症性过程的标志,识别这种细胞可使医师第一次对狼疮作出更快速更可靠的诊断。此后,哈格拉维斯医师及另一些学者很快发现了在周围血液标本中如何寻找狼疮细胞的方法,并证明70%~80%活动性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血液中都存在这种细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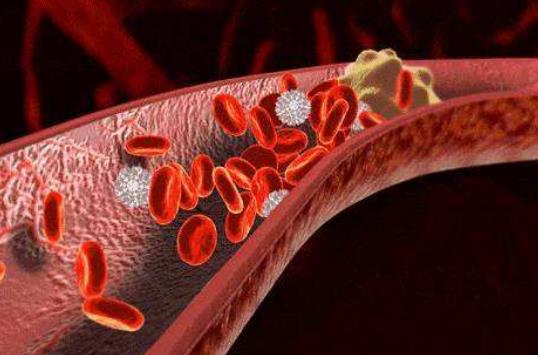
研究者们后浪推前浪滚动前进,如是,在以后的年代里不断有新的发现。例如在1949年玛约(Mayo)医院的另一临床医师菲利浦·韩琪(PhillipHench)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风湿病学家。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红斑狼疮业已风靡全世界,并魔术般地立即拯救了无数重症狼疮病人的生命。20世纪50年代,狼疮研究又出现了新的进展。许多研究者证明了癌症的化学治疗药物如氮芥能配合肾上腺皮质激素以有效地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严重脏器损害性并发症。

在了解狼疮的发展史后,已清楚地明白红斑狼疮一词系由西方国家命名。祖国医学即中医并无红斑狼疮一词,红斑狼疮的“疮”字同祖国医学所说的“疮”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有些人利用人们对狼疮的无知,打出祖传治“疮”的旗号。说自己是十几代中医祖传治“疮”专家,使得很多的红斑狼疮患者上当受骗。有人认为红斑狼疮同中国古代医籍中所形容的一些症状有些相同,如《金匮要略》中的阴阳毒相类似。阴阳毒是这样描述的:“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吐脓血……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疼如被杖。”如果我们仔细推敲这段话,就不难发现这与红斑狼疮是不同的概念,没有什么相似联系。还有一些人认为就本病的病名而言,根据本病的斑疹红赤如丹涂之状,形如蝴蝶,名之为“马缨丹”等,又因为红斑狼疮因日光暴晒而诱发或日晒后病情加重,名之为“日晒疮”、“鬼脸疮”等。这种认识实在有些牵强,因为很多的病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或因为太阳晒而出现面部斑疹,所以用中药治疗并不是强调我们的祖先曾经对红斑狼疮进行过研究,而应当以科学的态度,通过中医的方法学进行治疗,从中找出一些规律,发挥祖国医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来更好的为狼疮患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