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医闲暇,常看同仁处方,期偷师一二,每有获益。但也遇不少医者,处方之大,令吾惊叹:如此大方,非大医不能驾驭也。此处药方之大小,指方中药味之多少也。中医处方,古有七方之说,即大方、小方、急方、缓方、奇方、偶方、复方也。药味多少,《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有云:“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一般来说,只用二三味的方剂为小方,而13-15 味以上药物组成的方剂,即可称之为大方。
现不少医生开方,动辄十七八味,或20-30味,药物搭配,吾看不懂方义;药物使用,看不出主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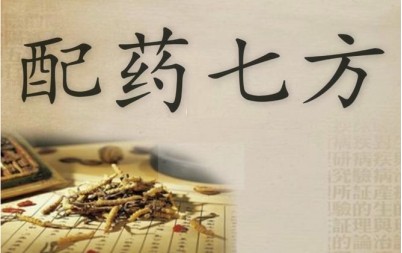
小方、大方之辩,自古便有。张仲景方被称为经方,是经过千百年来历代医生检验过的,是用之有效的,纵观其方,其药味并不多,是药简力专的典范。据统计:《伤寒论》收载方剂113首,《金匮要略》共收载方剂262首,大部分的汤剂均为10味药以下,15味药以上的只有两个方剂,分别是鳖甲煎丸(23味药),薯蓣丸(21味药)。张仲景被称为方剂之祖,其小方,为病人解决了不少痛厄,故此可见药并非越多越好。
如张仲景“芍药甘草汤”一方只二味药,药简效宏,功能:调和肝脾,缓急止痛。主治:伤寒伤阴,筋脉失濡,腿脚挛急,心烦,微恶寒,肝脾不和,脘腹疼痛。现代医学认为其方能:解痉、镇静、止痛、解热、抗炎、松弛平滑肌。有人谓仅持一方,加减运用,可行天下。《岁时广记》中,重用白芍,(芍甘5:1)专治疗脚气肿痛,叫脚肿汤;《朱氏集验方》中赤芍换芍药,谓“去杖方”,治脚弱无力,行步艰辛;《症因脉治》加黄连,治脾热泄泻不止,曰黄连戊己汤;《郑氏家传方》加川芎、白芷,治头痛、三叉神经痛。又芍药甘草汤加葛根治颈椎病;《单方验方选编》加赤芍、陈皮,治急性乳腺炎(乳痈);《医方妙用》加赤芍治疗痛经;《陈国华医案》中加川芎治面肌瘫痪;《伤寒论》中加桂枝治手臂痉挛。许多名方诸如八珍汤、逍遥散、柴胡疏肝散,都含有芍药甘草。

精于小方者多是大师。中医小方经历代医家反复锤炼,是诸多名方的组方基础,具有配伍关系稳定、量效关系确切、应用指征明确、价廉易于接受等特点。
隋唐名医许允(胤)宗曾言:“病之于药,有正相当,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自专,病即之愈。”许氏诊病,重视切脉,探求病原,主张病药相当,不宜杂药乱投,唯须单用一味,直攻病所。曾批评“不能识脉,莫识病原,以情臆意,多安药味”的医生。清王士雄亦言:一病原有一药主治,识之既真,何须多品?对于大方的流弊,《唐书.许允宗传》说:“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证,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病,不亦疏乎。”如此“围猎”,乱枪打鸟,照症配药,头痛川芎,发热柴胡,头晕天麻,眼干菊花,腹胀木香,嗳气陈皮,便秘大黄。攻补汗下,寒热温凉,升降沉浮,面面俱到。自以为“统筹兼顾”,“大面积撒网”,这么多味药,总会有一两个起作用吧。开药完全不顾标本、表里、寒热、虚实、真假、缓急。没有主证,没有八纲、经络、脏腑、气血、六经、营卫、三焦、病位的辩证,对证下药变成对症下药。胡子眉毛一把抓,机关枪、大炮一起上。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乱拳打死老师傅。能不能把病治好?连大夫自己都不知道!

大方的流弊,药味很多,非高手难以把控。药物之间会相互作用,相互反应,相互叠加,相互拮抗,相互制约,相互抵消。将诸多药物放进一锅中煮,放进肚子里消化吸收,酸甜苦辣咸,药物混合后,产生了哪些新的成分?产生什么作用?你得考虑:这么多药,口感如何?脾胃能否承受?杂粮粥一般也只有五味、八味吧?20多味食材一锅乱炖的暗黑料理,是否应该先找条狗试试会不会中毒?更何况药乎。你认为大方混合使用,产生了超越单味药本身的功效,你总得知道混合后新产生的是什么成分吧?
以往西医,出现一个病症,便加1-2味药。如你有高血压,便给你1-2个抗高血压的药;合并高血脂,便加降脂药;再有糖尿病,又给你1-2个降糖药;尿酸也高,再加降尿酸的药;再根据你的情况来几个治疗心脏、软化血管的药,还有胃病、慢阻肺、便秘、失眠等都得考虑,你同时服用的药物就会超出10余种。患者整天都活在疾病、服药的阴影中。近来,西医出现了一个特殊职业——叫临床药师,我们医院内称其为专门管医生的药剂师。经常可以看到患者到医院就医,同时挂好几个科室,比如同时挂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每个接诊医生都可能给患者开几味药,患者药单上的药物种类一直都在做加法,每天要服用的药物越来越多。这时我们可以去找临床药师,请他们看看你服用的药物是否有冲突,配伍是否合理,更重要的是临床药师会给你的药单做减法,尽可能减少同一时期服用药物的种类。我们病人看病时也应该带上自己正在服用的药物,请看诊医生帮我们做减法,而不是一味听医生给你加药。各科医生都有责任帮病人减药。
中医看病有自身的优势,即中医将人体看成一个整体,通过辩证施治,用一方一药治疗患者的全身情况。不能因为病人的病情复杂、兼证较多,就不辩主次,或蜻蜓点水、或撒胡椒、或普遍撒网、或乱抢打鸟,将方子垒的无限大。能否在:面面俱到与单刀直入、全面进攻与各个击破之间稍加考虑?我不一味反对大方,但你得知道什么是好方子?好方子,减了哪味都不行,添了一味也没用!
现在医院对药物都采取零差价售药。医生靠开贵重药材,什么人参、鹿茸、海马、冬虫夏草、藏红花,穿山甲……怎么贵便怎么来的现象可能很少见了。靠开大方去赚钱医生可能也少了。

另有主张大方的医生观点以为:现代环境变迁和现代生活的不良习惯导致疾病谱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现代人病多复杂且严重;其二是中药的耐药性;其三是现代药材质量下降。
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有人问过孙思邈:“古人用药至少,分两亦轻,瘥病极多;观君处方,非不烦重,分两亦多,而瘥病不及古人者,何也?”孙思邈回答说:“古者日月长远,药在土中,自养经久,气味真实,百姓少欲,禀气中和,感病轻微,易为医疗;今时日月短促,药力轻虚,人多巧诈,感病浓重,难以为医。病轻用药须少,疴重用药即多,此则医之一隅,何足怪也。又古之医有自将采取,阴干曝干,皆悉如法,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今之医者但知诊脉处方,不委采药时节,至于出处土地,新陈虚实,一皆不悉,所以治十不得五六者,寔由于此。夫处方者常须加意,重复用药,药乃有力,若学古人,徒自误耳,将来学者须详熟之。”
今人与唐代人比,病孰轻孰重?恐怕没有定论吧。今人对中药耐药,古人就不耐药吗?如今对中药材的栽培、采摘、储存、加工都制定了详细的规范,从何看出今药不如古药呢?单从药物加工看,南北朝雷敩撰写的《雷公炮炙论》早于孙思邈,其所载炮制药物才40余种;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炮制药物有140余种;明代缪希雍撰的《炮炙大法》是中国第二部炮制专著,收载了439种药物的炮制方法。难道不能反映中药质量总体在不断进步吗?我认为不同的病种,不同的病情,不同的治疗,不同的药物,不同的配伍,所需的药物大小多少大概都是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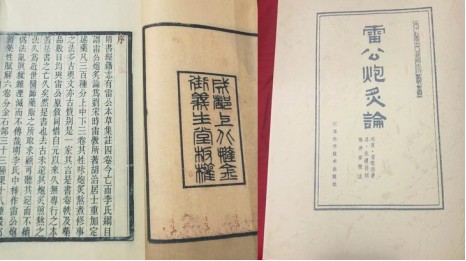
也许喜欢开大方的医生会说:实践证明大方的疗效好啊。许多名医也用大方。毋庸置疑,有不少著名的药方是大方,也有病人用大方获得良好疗效。这里有一个医生和病人的认知误区,看病的确要看疗效,但有效并不表示就是最好的。我们反对用疗效或有效率去误导病人。医生一辈子所干的事是:衡量药物或疗法对病人利弊孰大孰小。
另外,医学需要进步,精研古方,不拘泥古方,也是医学研究的一个方向。譬如苏合香丸,由15味药物(苏合香、安息香、冰片、水牛角、麝香、檀香、沉香、丁香、香附、木香、乳香、荜茇、白术、诃子肉、朱砂)组成。古代治疗卒心痛,现代医学用其治疗冠心病,并精简成由6味药组成(檀香、木香、乳香、朱砂、冰片、苏合香)的冠心苏合丸;进一步研究,简化为只有两味药组成的苏冰滴丸。这无疑是对该古方的阐扬。至于新开发的药方,还能否治疗原方主治的中风、吐泻等病症,则当是新的研究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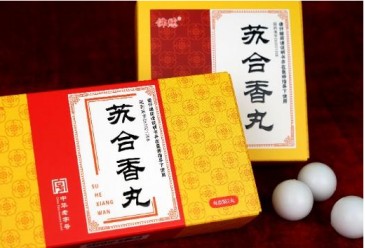
综上所述,大方、小方的存在都有一定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一些大方甚至有卓越疗效的。但不能说这就是尽善尽美的存在,删减大方为更有疗效、更少毒副作用的较小方剂,还是有可能的。这是临床医生的任务和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