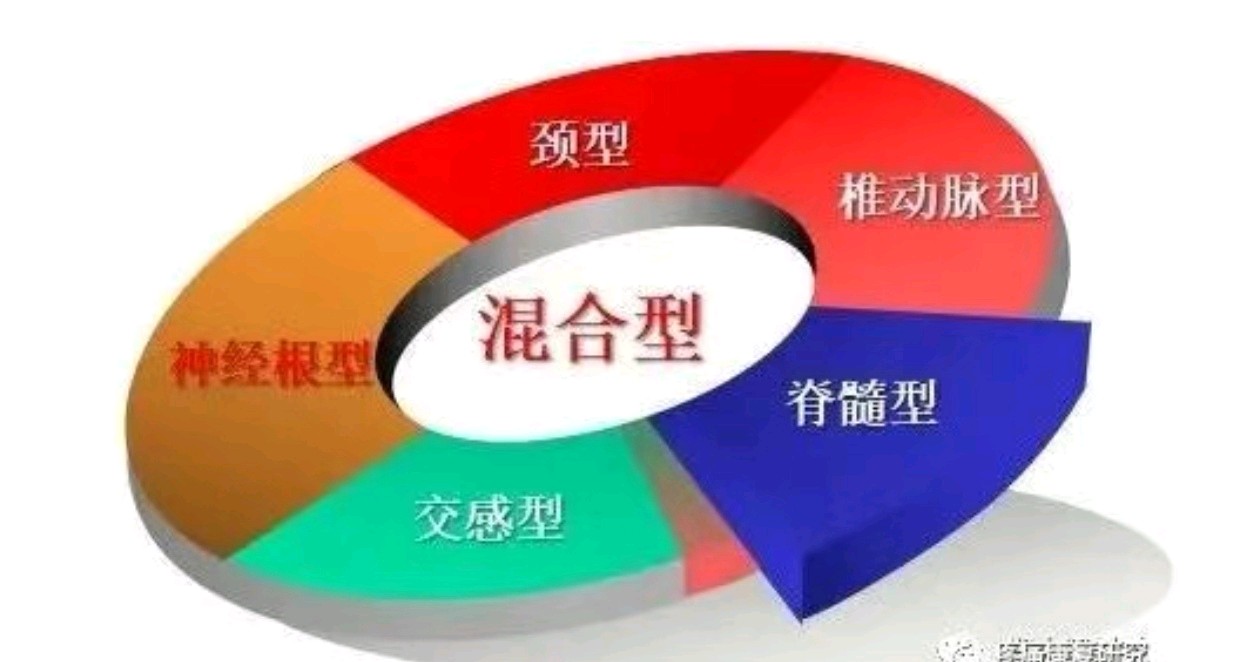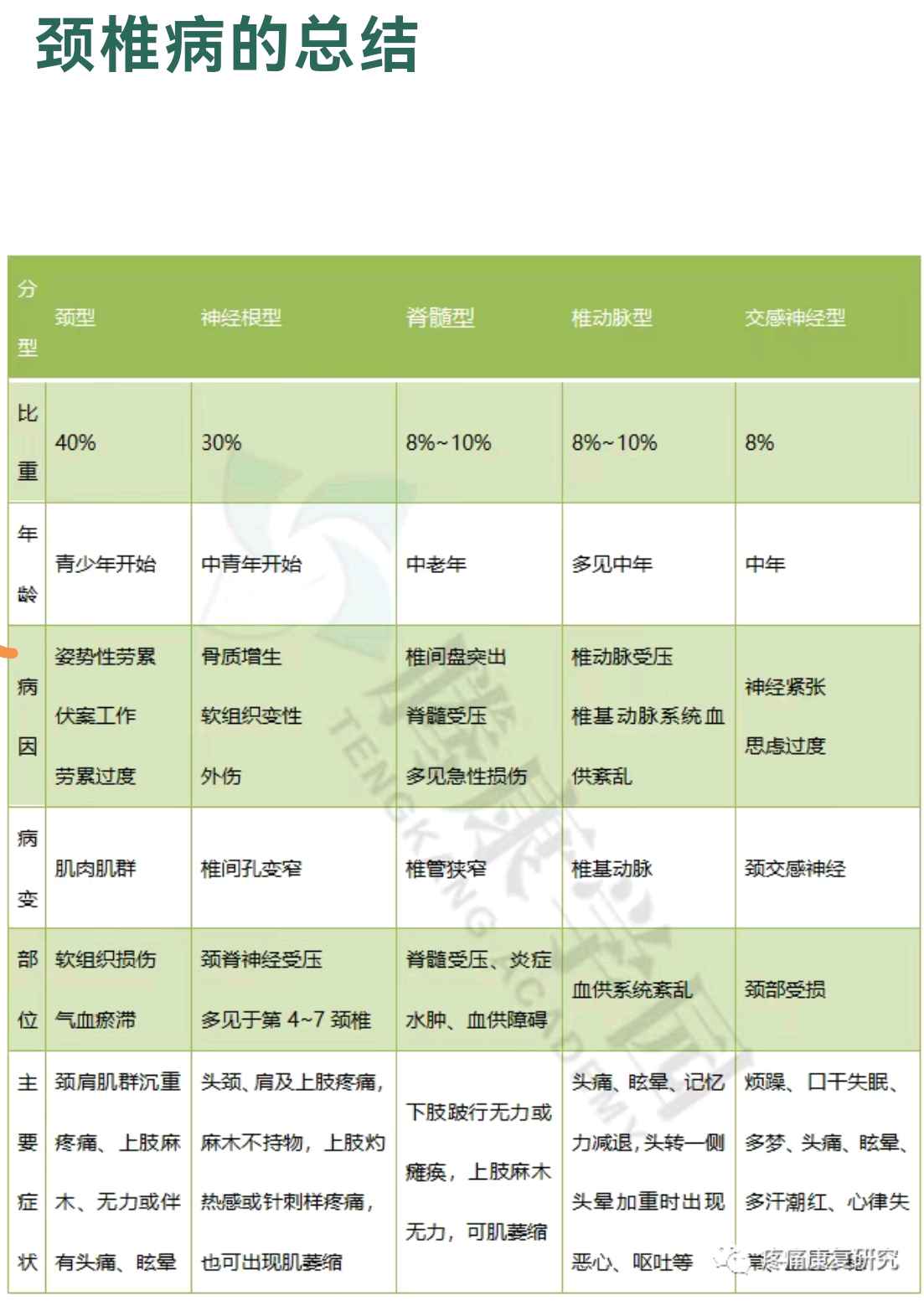颈椎病
朱家角的梅雨季刚收了尾,枕水居临河的荷塘就绽了花苞。周明拖着行李箱跨进“听雨”客房时,后颈的僵痛又缠了上来,像粒晒干的菱角壳,卡得骨缝生疼。他摸出止痛贴,正往脖子上糊,窗缝里溜进缕荷香——混着河水的腥甜,竟比城里的香水妥帖,叫人莫名静了几分。
晨雾漫过河面时,周明撞见了陈师傅。老人穿件洗得发白发亮的蓝布衫,裤脚卷到膝头,正撑着乌篷船给塘里的荷浇水。铜壶滋啦滋啦响,水珠溅在荷叶上,碎成晶亮的星子。“小伙子,你这脖子,跟我塘里的荷茎似的——该直不直,该弯不弯。”陈师傅的船桨轻轻一点,乌篷船便转了个圈,荷香扑得周明打了个喷嚏。
周明苦笑着指颈间:“陈师傅好眼力,这是互联网人的‘职业勋章’。”陈师傅却笑,往他手里塞片荷叶:“我从前是推拿师,现在给客栈撑船、侍弄花木。你看这荷茎,中空外直,能扛住风雨,全靠里头那股舒展的气。颈椎也一样,得有弧度,才经得住折腾。”
陈师傅摸进“听雨”房时,周明正蜷在临河书案前改方案,颈子几乎要贴到键盘上。老人从蓝布兜里掏出本卷边的《人间草木》:“垫在电脑下,写草木,也写生活的筋骨。”周明依言把书垫上,屏幕刚好齐眉,腰背也跟着挺直——倒像被人把弯了的竹篾猛地扳正了。陈师傅又指着床头的蓝印花布枕:“硬枕折成荷苞的形状,托着颈窝;软枕留着午睡用,别让脖子空落落的。”说着从裤兜摸出个竹编铃铛,“每小时摇铃起身,绕着河走两圈,看看我养的荷。”
此后每晨,周明都跟着陈师傅在塘边的老柳树下做操。仰头看花苞顶的晨露,像悬在半空的水晶盏;低头闻荷叶的腥甜,仿佛要衔住自己的衣领;侧屈时碰着荷叶的凉,颈侧的肌肉竟跟着松快起来,像春河冰裂时的舒展。“您这操,倒像在跟荷花打招呼。”周明笑着转脖子,骨缝里的酸胀慢慢化开。陈师傅往他手里塞颗莲蓬:“荷茎能挺,靠的是中空;颈椎要舒,得学荷茎里的空劲儿——别把自己绷成实心竹竿。”
周明去见古镇开发方时,车把上挂着串莲蓬——是廊桥边阿婆塞的。阿婆穿蓝布衫,挎着竹篮,笑说“荷香养人”。骑车过永安桥,梧桐影落在颈间,风里裹着荷香,竟比从前松快许多。谈判设在临河茶馆,周明挺直的腰背里,藏着这几日悟到的舒展。回枕水居时,陈师傅正往塘里添水:“你看这荷叶,雨天承露,晴天遮阳,从不跟自己较劲。人也一样,脖子顺了,心气也顺。”周明望着塘里的花苞,忽觉这趟差旅,竟在颈间的酸痛里,咂摸出汪曾祺写的“人间情味”——就像阿婆茶里的芡实糕,糯糯的,裹着草木香。
离开前晚,陈师傅敲开“听雨”房的木窗,递来本新的《受戒》,夹着片晒干的荷叶:“颈子舒展了,心也敞亮。往后别把自己绷太紧,像荷茎那样,空着,才扛得住风雨。”
周明抱着书站在塘边,暮色里的荷塘泛着柔光。颈间的弧度像荷茎般自在,朱家角的风掠过,恍惚又听见陈师傅撑乌篷船的吱呀声,滋啦滋啦,把生活里的僵劲,都浇成了舒展的模样。塘里的荷影晃啊晃,连对岸茶馆的阿婆茶香气,都成了颈间最温柔的余韵。
作者 乡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