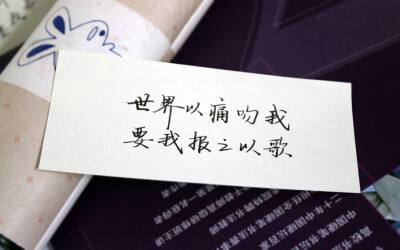“白医生(化名),急诊患者来了。”护士的呼唤声打破了病区的宁静。
那是一个盛夏的午后,120工作人员用急救车从本市某三甲医院转运过来一个女性患者。输液架上有1个3L袋(全肠外营养配置装置)、2个微量输液泵(舒芬太尼+奥曲肽),患者用鼻氧管吸氧状态,连着心电监测仪。很明显,这是一个癌症重症患者。
作为当天的值班医生,白医生自然是患者的首诊医生,第一时间赶到护士站对面的23床。约定俗成,距离护士站、医生办公室最近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也许因为长期的抗癌治疗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患者像受伤的小猫一样蜷缩在并不宽大的病床上,耷拉着脑袋,面部冲着左下方,汗湿的头发散乱地贴在额头及脸上,以至于完全看不清她的模样。不过,瞄一眼旁边的微量输液泵,白医生就对她的病情有了八九不离十的初步判定和评估。

凭着职业敏感性,尚未询问病史,白医生就知道患者的癌痛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她应该是重度癌痛患者无疑,需要紧急做进一步处理。陪伴患者的是3位男士,中年男性是患者父亲,另外两位年轻男士是患者的丈夫和弟弟。通过患者丈夫口述结合手机中的碎片电子资料得知,患者脐尿管二次术后复发进展,当前出现盆腹腔多发转移,多发骨转移,癌症病情进入晚期阶段,难治性重度癌痛、恶性肠梗阻、肿瘤破裂待排、电解质紊乱、肾功能不全。白医生迅速采集完病史,再次回到床边,尝试近距离与患者进行沟通并查体。
“你好,我是你的管床医生白医生,我知道你现在很痛,不过还是要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和做几项,查体你只需要点头或者摇头就好。”患者丈夫在床边静静拉着她的左手。

患者艰难地把头转向右侧,然后腾挪了好久才转过身来,正面对着白医生,脸部表情因持续的疼痛而扭曲。白医生的手刚触碰到她的腹部,患者就大叫一声“啊!疼!”身体瞬间收回到之前的左侧卧位。
“嘀、嘀、嘀嘀……”因患者生命体征的波动,床边的心电监护仪不时发出警报声,伴随着指示灯的闪烁。
作为一位已经在临床摸爬滚打近10年的高年资专科医生,白医生顿了顿,整理了一下思绪,与家属进行了第一次深入交流。

“缓解疼痛是当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天口服840mg盐酸羟考酮也无法有效控制疼痛,那就要联合应用静脉镇静了。肿瘤的进展伴随着恶性肠梗阻,结合昨天外院的腹部增强螺旋计算机断层扫描 (computed tomography,CT) 检查,左侧附件肿物破裂出血不能排除,可能需要再次复查CT或急诊手术。”白医生知道必须先给家属交代清楚患者病情,并当面询问是否同意在患者病情进一步恶化后采取气管插管、气管切开、胸外压、电除颤等有创抢救措施。家属不约而同地犹豫了,谁也没有说话。
“你们先考虑一下,一个小时后我们再沟通,或者等你们想好了随时来找我。”白医生知道此时家属需要一个缓冲期。是的,这个抉择太难,其中不免夹杂着惶恐、不知所措、害怕、顾虑重重等各种个人、家庭及社会因素。
暴发痛处理、评估内环境、营养支持、维持水电解质平稳等一系列对症支持处理后,家属仍然没有作出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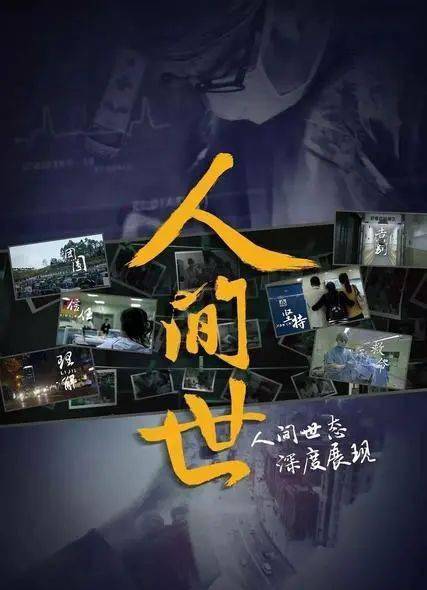
“插管痛苦吗?”“上呼吸机会难受吗?”“听说胸外按压可能会压断肋骨?”“进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一天的费用是多少?家属能去里边探视吗?”“做这么多治疗能把疼痛和肿瘤控制住吗?”“肿瘤破裂后还有手术机会吗?”3位家属你一句我一句地抛出多个问题。
白医生理解家属的担忧,把一个个问题记录在查房本上,准备逐个回答。“不管气管插管还是上呼吸机辅助通气,胸外按压等都是有创抢救措施,有不可避免的二次致命损伤。如果进了ICU,会用一些生命支持设备,加上相关药物及检验检查,费用肯定不会低。现在属于疫情管控期间,家属是不能陪同探视的……”
家属还是很犹豫,不能下定决心作出选择。
吗啡针暴发痛处理、进行性加大镇静镇痛泵静脉用药剂量,白医生多次向护士发出调整医嘱指令。患者的癌痛在短时间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不断发出哀嚎声,冲击着家属的心,也刺激着医护人员的神经。病人因疼痛不断发出小猫一般的哀嚎声,一声接着声叫喊声,不仅冲击着床边患者家属的心房,每一声哀嚎也刺激着当天每一位值班医护人员的神经。在爆发性疼痛出现的时候,她爱人除了握着患者的手或者干脆抱住那蜷缩而颤抖的身躯外别他法,父亲和弟弟拽束手无策神情呆滞站在床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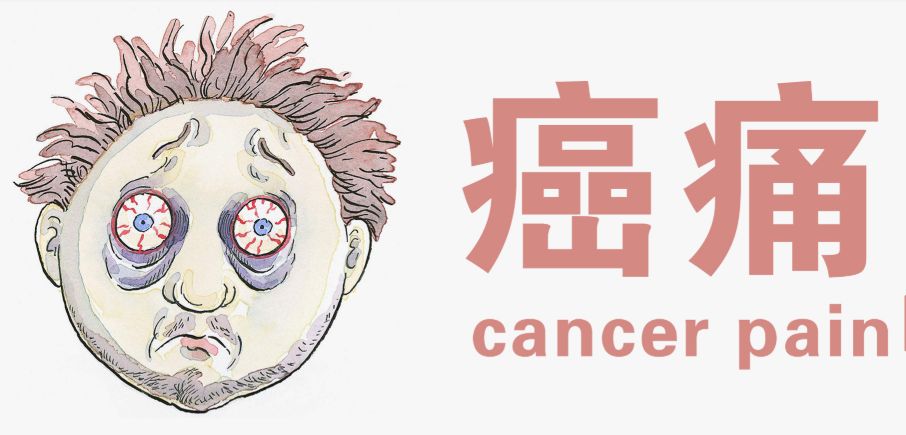
晚上8点,结合普外科、麻醉科及ICU专科医生的会诊意见,白医生决定再次召集家属进行沟通。
看向白医生的3双眼睛里多了一分无奈,少了一分期待。
白医生:“对于肿瘤本身,患者在外院已经接受过多种内外科治疗方式,疾病的预后和转归你们也应该非常清楚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做的一些处理,临床疗效并不理想。”
患者爱人默默点头,眼神有些飘忽,但紧接表示只要有合适的方法,他们都愿意尝试。
患者父亲和弟弟没有说什么,只是互相看了看对方,一脸茫然。
白医生开始跟他们探讨各种决策的利弊和风险,“如果选择外科干预,有两种可能,一是暂时解除恶性梗阻,疼痛得到改善,但是肿瘤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二是肿瘤破裂,无法进行手术干预,只能停止手术,患者甚至可能下不来手术台。如果选择微创介入治疗,在麻醉科评估后做局部神经浸润麻醉,通过局部微导管持续泵入复合型镇痛镇静用药,但是考虑患者当前的一般状况,出现呼吸心跳骤停等意外的风险极高。另外,使用大剂量的麻醉镇静镇痛药物仍旧无效后,是否考虑选择转ICU,在严密监护及高级生命支持下处理癌痛问题?如果进行了气管切开或者气管插管,患者基本不可能从ICU出来的,异地医保费用问题也是你们要认真考虑的……”
这次,白医生掰开了揉碎了解释,3位家属听得频频点头。他们告诉白医生需要10分钟时间来商量并做选择。
可10分钟后,他们依旧没有作出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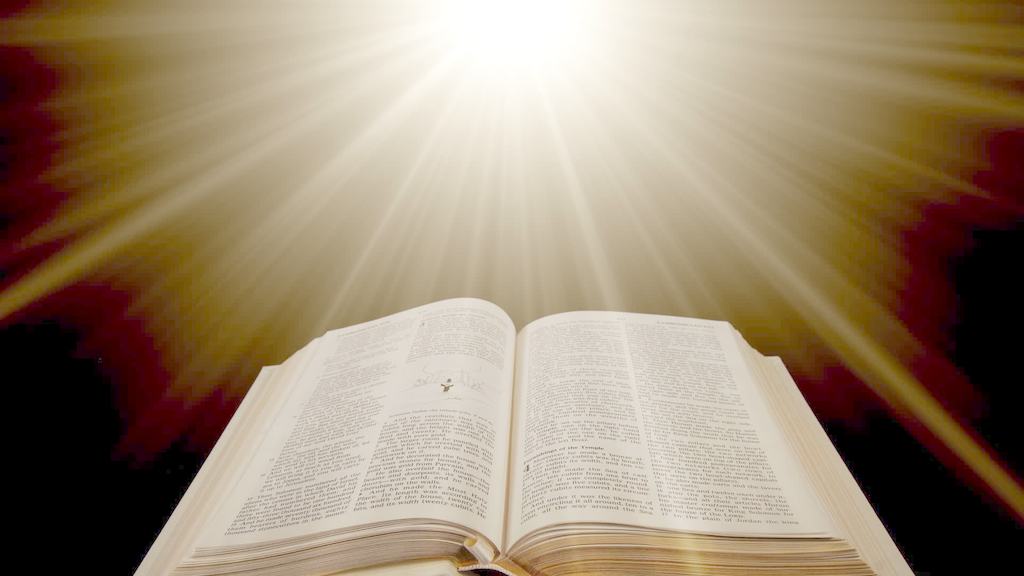
白医生停下手中的工作,抬头看着墙上那句“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沉思了一会,然后将患者丈夫单独请进医生办公室。
“你知道妻子现在的担忧和真实想法吗?你觉得妻子现在最需要什么?如果疾病不能被治愈,对妻子来说最好的归宿是什么?”白医生直接抛出3个问题。
“我们夫妻两人一起在深圳打拼10年了,孩子在老家刚上小学一年级。其实我知道这个病治是治不好的,两次手术及前后的多次治疗几乎耗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我现在只希望可以让她不那么痛苦。夫妻一场,这辈子不能走到最后,但愿她能笑着离开。”患者丈夫的泪水夺眶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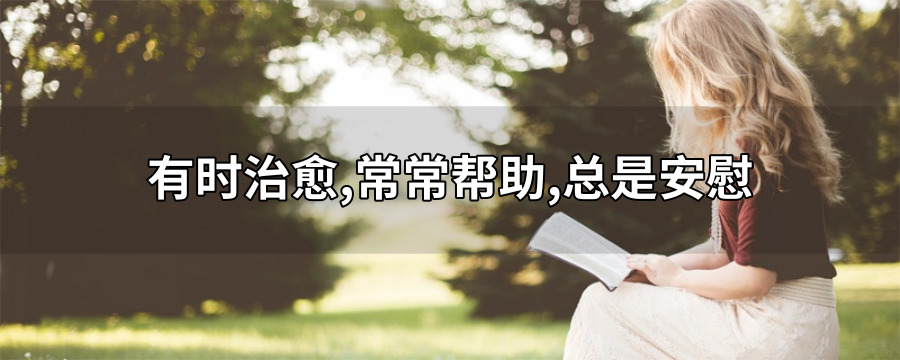
白医生拉开抽屉,递上早已备好的纸巾,他明白家属需要情绪的释放。这些年经历多次“生命尽头的对话”,已经让他练就了在这种时刻保持清醒和理性,适时共情又能给予引导和帮助,并参与和促成临床决策的能力。
接下来白医生分享了两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是胰腺癌晚期患者和老伴儿选择安宁疗护场所的故事,一个是年轻的卵巢癌妈妈和2岁女儿告别的故事,借此给患者丈夫一些引导,其本质是死亡教育和叙事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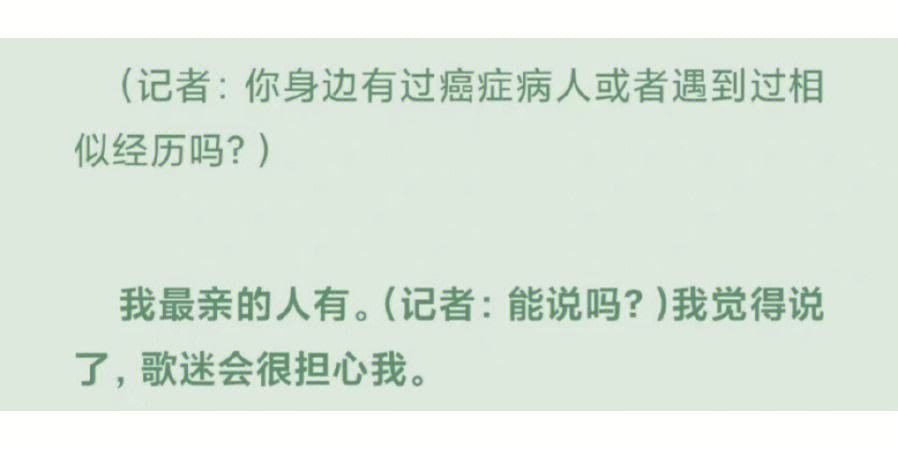
深夜11点,在家属取得一致意见后,白医生请麻醉科做了局部浸润麻醉。
后半夜,患者睡着了。
次日,家属联系120救护车转运至当地医院进行安宁疗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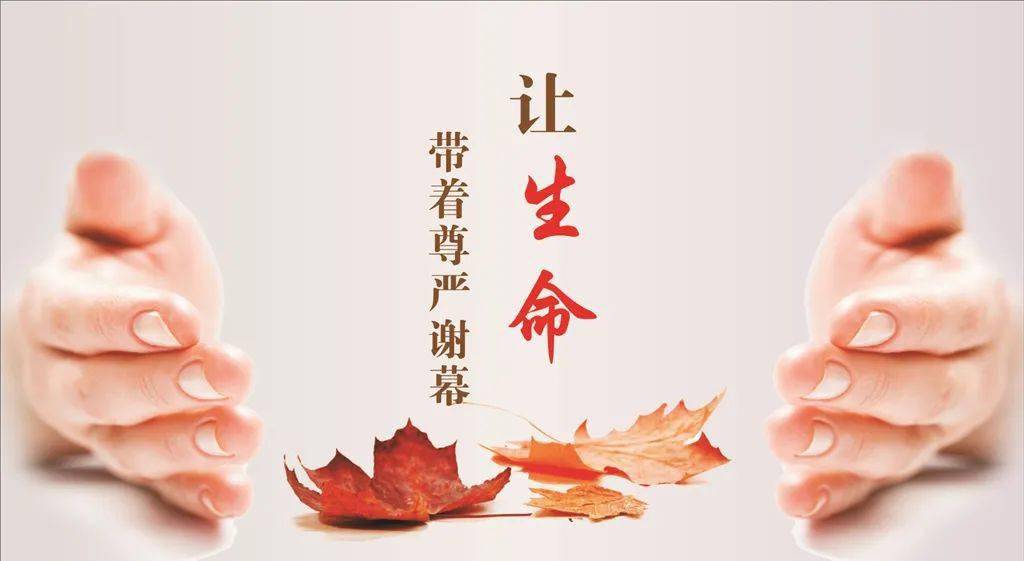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第167节有这么一句话:“世界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世界给我们带来了痛苦和磨难,但是我们不应该消极面对,这个世界仍然是美丽的,我们应该把这些困难作为锻炼,以此获得经验。
作为肿瘤专科医生,如何以“歌声”回应病痛,也许叙事医学就是独特的重要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