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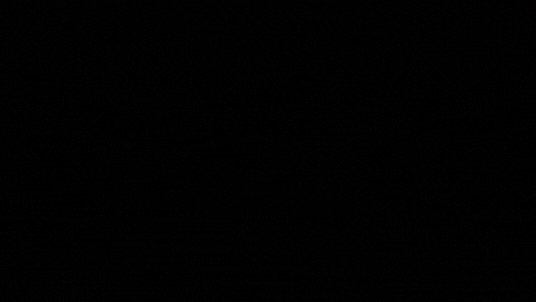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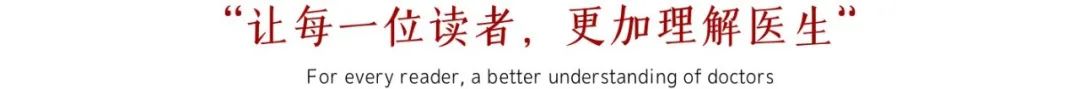
同情心本属人类的自然情感,可对外科医生来说,却实在是种需打磨的技术活。

可以说,医生努力的其中一个面向,就是学会把同情心转化为积极的、可操作的专业行动。
有些拗口,我慢慢写。
首先不同于常人的是,医生必须面对同情的困境。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每逢社会中不幸发生,或天灾、或人祸、或异国的战争,手机上的相关消息铺天盖地,读起来总令人难过。
翻阅十数条之后,终于心力交瘁,不忍再读。
这些事实就如此过去,不会影响第二早醒来的我们。
毕竟那是远方的哭声,毕竟放下手机,就可以回归到正常生活之中。

《摄影师眼中的伊拉克战争》(2004)
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中曾写,“毕其一生,每个人只不过有时间给少数几个人以关爱。我们凡人所能做到的,恐怕只能够是爱比较亲近的人。”
针对人之精力与同情的悖论,彼得斯的答案是,那就关爱少数的眼前人吧。
可医生的困境正在于此,因为所听闻的哭声并不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近处;因为需要你付出关爱的,每一个都是眼前人。
同情已是不易,可医生的职责,又无法仅止于同情。

每次术前洗手,既是消毒,也是医生让自己心灵清零的一种仪式。
无论我们在接诊与查房时怀着何种关怀,也务必把这种同情心全部留在手术室外,避免情感波动干扰判断。
又要借旁人言,茨威格的小说《心灵的焦灼》中,康尔多医生就有这样一段论断。
“我有一次曾经警告过您,同情心这玩意,可是他妈的一把两面双刃的东西。谁要是不会摆弄,趁早撒手,尤其要稳住自己的心。”
“同情就跟吗啡一样,只有在刚开头的时候对病人是行善,是灵药,是帮助,可是如果你不会掌握分寸,剂量不当,不及时停药,就会变成凶险的毒药。”

的确是这样,当你面对求医无处的患者时,要想到他是谁的父亲、又是谁的儿子。
但只要上了手术台,就不要再去多看他的脸庞,腹腔打开,他就谁也不是,眼前所见的只有一套急需谨慎应对、仔细修复的生命系统。
悲心如水,智慧如舟。手术的技艺,同情心的收放与张弛,就是医生为自己所作的舟,避免将自己与患者都倾覆吞没于同情心之中。

写到这里,读者大概就明白为何同情之于医生,是一门技术活了。
因它不仅需要充沛、还需要分寸,更需要“行于应至,止于当止。”
尽管它是克制的,但文章结尾处,却想毫无克制地去赞颂医者的此种情感。

因为这世上有两种同情,其中一种怯懦感伤,它不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只是害怕它触及自己的心灵,才用同情将其隔断开来保护自我。
而医生所具备的同情,是另一种积极的、勇敢的同情,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